跟隨阿來 去有風的曠野 見萬物見自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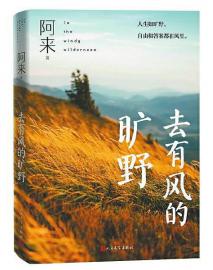

阿來在巴朗山拍花。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肖姍姍攝

阿來行走于高原。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肖姍姍攝
人生如曠野,自由和答案都在風里。有風到達的地方,散落著生活的詩意。看過青山和飛鳥,眼睛會重新變得清澈。曠野之息,在那里,我們看見生命,找到自己……9月的最后一天,著名作家阿來2024年散文新作《去有風的曠野》正式上市。該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,10個把心交給曠野的故事,是阿來漫步遠山的誠意之作。
阿來不僅是作家,更是行走文學的踐行者,還是深藏不露的博物學家。無論是四姑娘山的秋景、米倉山脈的云海,還是稻城亞丁的巖石,在他的筆下,都不僅是自然風光,更是通過它們探討人與自然、人與自己的關系。他說,行走讓我們認識世界、深入世界、呈現(xiàn)世界,這樣人生才可能走向開闊。
拿到書后,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與阿來進行了一場漫談;在2024天府書展上,阿來也與作家徐則臣、馬伯庸聊了“曠野”背后的故事。阿來讓讀者們懂得,“曠野”不只是遠方,它并非遙不可及,它就隱藏在我們?nèi)粘I畹目p隙里。
把心交給曠野將行走和寫作視作宿命
對常年奔波在鋼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來說,想開辟一方讓時間慢下來的天地,似乎成了奢侈。阿來始終拒絕讓快節(jié)奏的生活將自己的人生變成段子,在他看來,人生是一個漫長、緩慢的進程,沒有那么短。于是,他選擇把心交給曠野,以一個他者的身份,去探尋種種奇遇。每每深入一片土地,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了下來。
阿來寫道:“一個小時走5公里和一個小時飛720公里,看到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。”“大自然有時候能給人提供一種慰藉,所以我總是要抽時間從河谷地帶的人間社會出去,經(jīng)過人間,最后到?jīng)]有人間的自然中去,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,它的美麗會給你安慰。”
《去有風的曠野》收錄的是阿來的10個行走往事。包括《十二背后》《四姑娘山行記》《莫格德哇行記》《分云撥霧見米倉》《稻城亞丁行記》《再訪米倉山三記》《扎谿卡行記》《爐霍行記》《大涼山訪杜鵑花記》《薔薇科的兩個春天》。阿來說:“時代在以我們并不清楚的方式加快它的步伐,總有一個聲音在催促,快,快!卻又不告訴我們哪里是終點,是一個什么樣的終點。”所以,他一直走,一直走。
在《十二背后》,他借由喀斯特溶洞遙想巖石幾億年的歷史。“緩慢,從容,水蝕石穿,不慌不忙。人的生命短暫,地球自己卻有的是時間。”置身其間,一切都凝固無言,只感覺造化的偉力,只感到地老天荒。
在莫格德哇,他躺在草地上靜享世界無聲,山峙水環(huán)。回望當年的古戰(zhàn)場,如今草色彌天,牛羊蔽野;他在墓群遺跡旁,細數(shù)生生不息的族群與文化;在稻城亞丁,“吃蔬菜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人,吃肉覺得自己成了某種兇猛動物。吃飽了蘑菇,我覺得自己變成了一棵樹。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覺,但我確實覺得自己成了一棵香氣充滿的樹。而在樹下,一場細雨后,拱破泥土,生出了那么多的蘑菇。”
多年來,阿來始終將行走和寫作視作宿命,攀行在曠野之間,任群山的波濤把身體充滿,抬頭仰望蒼穹星辰,俯身凝視花草生靈。誠如馬伯庸所說:“阿來對于自然的理解、對于自然的親近,一定并不僅僅局限在思考上,他一定會身體力行。”
馬伯庸回憶,在一場綜藝節(jié)目錄制時,阿來與他在清晨的一株青草前相遇。阿來如數(shù)家珍地為他介紹一草一木,讓馬伯庸瞬感“寧靜平和”。“以前看景色,我都會焦慮自己是否可以把這些素材寫進小說,但那天清晨,我真的覺得整個人特別放松與純粹。”他笑稱,這個不經(jīng)意的小片段還被編導發(fā)現(xiàn),一群人“連滾帶爬”地扛著設備來抓住這一時刻。
除領教到阿來隱藏的植物學家身份,馬伯庸還在《去有風的曠野》中,發(fā)現(xiàn)了阿來風景語言中隱藏的另一番奇幻的詩意。在書中有這樣一句話——這些怪獸是在用幾千萬年的巖石嗓子發(fā)出聲音。“這句話甚至可以延伸出一部非常驚艷的幻想故事。”馬伯庸認為,可以把這部書當作探險小說來看,“仿佛親臨現(xiàn)場,是個非常好的解壓方式。”
敞開生命感受自然與人文之美
在《去有風的曠野》中,阿來呈現(xiàn)了他作為一位植物學的癡迷者和博學者的一面,他的文章無一不聚焦花草樹木,棘豆、風花菊、香青、蠅子草……他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,對每一株看似無名的花草如數(shù)家珍。
在他的手機和電腦硬盤里,儲存了數(shù)萬張植物圖片,因而他被讀者們親切地稱為“作家中的植物學家”。
他記錄自己趴在地上,把鏡頭對準一株貼著地面匍匐生長的豆莢:“用肉眼打量,再端起相機細細打量。不同的距離,不同的視點。”看它們呈現(xiàn)形狀個個不同的葉與花,摁下快門后,因憋氣而躺倒在草地上,偶遇一片湛藍的天空。“眼前藍空由虛幻而變成真切,靜默如淵,其深如海。”
正因為阿來對大地有著與常人不一樣的愛意與執(zhí)著,他希望能記住這塊土地的所有,包括每個動物和植物的名字。“我們在大地上行走,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、文化史,知道這些生命體的名字,才能書寫這片大地、獲得個人和社會的生命體驗。”他說:“我是一個愛植物的人。愛植物,自然就會更愛它們開放的花朵。”
他的文字因此有了另一層質(zhì)感,風景不再是人物活動的“背景板”,鮮紅的杜鵑、紫色的馬先蒿、藍黃相間的鳶尾,生機處處;云杉、白樺、杉樹、松柏,蓊郁如海。他的文字總有一股自然的野氣,穿行于群山中,頭頂藍天,看冰川消融、古樹繁花。
談及他對自然的珍視和熱愛,他說,主要源于自己長期在四川、西藏、青海、甘肅、云南等地的田野調(diào)查和走訪考察。正因為看到和感受到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的影響,所以希望中國的生態(tài)文學作為一個問題、一種文學樣式,承擔其責任使命,表現(xiàn)和揭示社會面臨的生態(tài)問題,探尋生態(tài)危機的根源,從而以作品表達作家的倫理觀照、審美追求和社會擔當,引導和助力社會重塑心靈生態(tài)、建設生態(tài)文明。
“如果把地球的歷史變成一天的24小時,人就是這一天最后兩三分鐘出現(xiàn)的。”阿來向記者說了這樣一句話。在他看來,天下眾生不只眾人之眾,而是所有生命。“大自然就是一場生命奇跡,人只是眾多奇跡中的一個奇跡。如果沒有自然環(huán)境,人的生命會失去依托。因為人不是在地球上孤零零存在的,相伴的,還有植物、動物。人是地球上最晚出現(xiàn)的生命,有什么道理不去尊重其他的生命?”
阿來常常為人類漠視自然而感到痛心。他回憶,在一個大雪天,當他在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峰后,終于找到100多年前被植物學家威爾遜記錄下的綠絨蒿,感嘆其在天地間獨一無二的美麗時,一群前來游玩的大學生上前問他,知不知道這里最紅的那個網(wǎng)紅打卡景點在哪里?
“他們身處那么漂亮的原野中,坐在那么高的雪山上,一臉茫然地問了我這個問題。”阿來感到可笑也感到可惜,他嘆息:“我還是那句話,我不能忍受自己對置身的環(huán)境一無所知。行走還是要有一種態(tài)度,要帶著對大自然的熱愛與好奇心,同時也帶著足夠的知識儲備。這樣走到永恒的曠野,就不是去打卡,而是敞開生命,去感受自然與人文之美。”
透過“阿來式”散文觸摸自然文學全新審美
好的旅行寫作,不僅能呈現(xiàn)那些遙遠而新鮮的風景,讓讀者通過文字的介質(zhì)感受曠野之息,也能經(jīng)由作家筆下獨特的山脈水文,將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復的旅程。
相比行走,阿來認為,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,他的文字處處透露著人生哲學與豁達。“我孤身而行,覺得越走越有勁,每天幾十里。都沒準備,就身上那點零花錢。走到哪里,找個老鄉(xiāng)家吃住。一路覺得很過癮,好多問題好像能夠得到解答。從低地往高處走,都是大山大河。”“人看到的不只是美麗的大自然,也能看到自己深藏不露的內(nèi)心世界。”
在米倉山巔,他毫不失望于時值紅葉節(jié)而未見紅葉,反而慶幸賞到了盛放的杜鵑,“大可不必因為未見紅葉,而失望,而抱怨,不必非見一種規(guī)定性的秋天。既有夏天如此絢麗的杜鵑花海,為何一直只說那些紅葉?”
在金川河谷賞梨花,他看到了因一場戰(zhàn)事造就的梨花的前世今生,“所以,我看到了不同植物所根植的不同地理與文化。所以,我看到了一年之中,不同海拔高度上,薔薇科植物開出了兩個春天。”
在莫格德哇,他走在“水沮洳散渙,方可七八十里”“且泥淖溺,不勝人跡”的沼澤地里,心里沒有畏懼,反而覺得“腳踩過這么柔軟的草與泥與水,真的是地闊天低,思接萬里”。走出這片沼澤時,他回身向鳥微笑,向花微笑。
閑聊時,阿來還跟記者分享,他攀登到一座很高的山上,口渴難耐時,在足下看到一洼一洼的積水。水下是泥,而靜置的水又是那般清澈。他俯下身去,用嘴去吸吮,“這是大自然的恩賜。”
“曠野之息,在那里,我們看見生命,找到自己。”阿來坦言,《去有風的曠野》里的10篇文章,寫作的過程也是他學習、體會的過程。“我在慢慢學習,不光是在書里寫有關自然的故事,我也學會在大自然中去尋找、去理解大自然的美好,接近它們,傾聽它們,擁抱它們,感受它們,最后確確實實發(fā)現(xiàn)自己正在脫胎換骨。”
但阿來認為,光他一個人學習和寫作是遠遠不夠的,中國文學對更廣大共生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關照與關懷太少。在中國的敘事文學中,“自然”已經(jīng)有非常非常長的時間不存在了,以至于我們會忘記“自然”。
在《去有風的曠野》中,阿來展現(xiàn)了他在地理學、植物學、動物學等方面的專業(yè)性,發(fā)起了自然文學的全新審美實踐。“寫植物,你得清楚它長在什么地方,要寫清楚它的生長環(huán)境,這又牽涉到另一門知識,地質(zhì)學。然后,高山垂直,下面是亞熱帶,中間是溫帶,上面是寒帶,這又要說到氣候?qū)W……每一次寫作,都幫我推開一扇知識的大門。”
談及自然寫作的現(xiàn)狀,徐則臣也深有感觸。他點出文壇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:小說家包括寫散文的作家、詩人等,脫離了房間,脫離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,出了門,就會覺得“無話可說”。
徐則臣直言,知識儲備專業(yè)背景的缺少是其次,將風景與事物與人之間聯(lián)系起來建立關系是主要難點,“當今的文學主要是寫人的文學,但在文學里,應有一個人和世界的關系。所以,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啟發(fā),我們?nèi)绾蚊枋鑫覀兣c世界的關系,我們應如何在世界上定位。”
徐則臣強調(diào),具有宏大整體感的散文,在當今的散文中是稀缺的。將自我放在歷史中、放在天地間的思考者少之又少,而這些正是“阿來式”散文的特點。
□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肖姍姍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 關注人民網(wǎng),傳播正能量
關注人民網(wǎng),傳播正能量